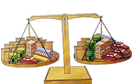
最近在美國與英國都在談論如何讓經濟重新恢復平衡;此舉似乎意味著設法讓經濟不再依賴於金融業以及鼓勵製造業的發展,或許也可能意味著英國要重新處理相對富裕的南部地區與失業率高企的北部地區的發展失衡問題。
這種探討還不夠深入;如今需要扭轉失衡的不僅僅是一、二項問題,而是有好幾項。激進歷史學家與生態學家伊萬•伊里奇(Ivan Illich, 1926-2002)在其廣泛流傳的著作《陶然自得的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中使用的術語是“多點平衡”。事實上,伊里奇確定了“相輔相成的六大重點,每一種都會讓生活向某一方向失衡”。
在伊里奇看來,第一個失常的平衡是“人類與生物圈之間的脆弱平衡”。在酸雨、臭氧層損耗以及全球變暖這類問題成為世人關註的重點前,他就一直警示世人:我們的星球正遭受無節制的污染氣體排放、有毒氣體以及過量開採礦產資源的威脅。這樣的警示如今變得老生常談,但讓伊里奇特別有吸引力的是其不接受常規手段來修正全球失衡問題。他看到應對污染的技術若是沒有輔以人類價值觀的深刻變化,只會是“把垃圾轉移到看不見的地方、把它們推給子孫後代以及傾倒到窮國”。
伊里奇的解決方案並不在於應用先進科技處理“已然存在的環境問題”,而是讓人類捫心自問,探究到底是什麽導致了今天的危機。他在書中寫道,“處理環境危機的唯一齣路是人類共同認識到只有精誠合作、休戚與共,方能生活得更為幸福。”伊里奇反對這樣的說法,即機器可以代替人類做大部分的工作,同時至少不會出現這樣的不良結果:人類因從事過度生產與過度消費等單調乏味的工作而變成機器的奴隸。他的這一看法頗具爭議,但更具爭議的是:他強烈反對把醫療與教育機構化,認為是把與生俱有的能力置於產業化的龐大機構手中。
這些就是工作(即讓人愉悅、創意無限的工作)以及學習的失衡的情況。更為嚴重的失衡情況包括了過去與現在(在如今這個一切都是有計劃荒廢的時代,過去顯得越來越與現在脫節)以及富人與窮人。
這些失衡情況是如何疊加在一起的?當前解決環境與生態危機(自1973年以來,人為造成的全球變暖、海洋酸化以及物種的大量毀滅的證據觸目驚心,使得危機愈發嚴重)的出路似乎是伊里奇未曾想到的:人類自己的掩耳盜鈴。當艾登堡(David Attenborough)在BBC播出的《冰凍的星球》(Frozen Planet) 電視系列片中提醒世人註意這些問題時,他被某些地區的人指責是極端分子。西蒙•庫柏(Simon Kuper)這樣寫道:“西方人最近打了個未說出口的賭:打算加速環境惡化,並甘冒氣候災難的風險,最後冀希望由遙遠的窮國百姓去承受這一切。”
說到工作的失衡,與其說採取伊里奇所提出的更為激進的舉措,讓人類的工作變得人性化與創意十足,倒不如說我們更多談及的是工作與生活之間的關系失常問題。我們似乎老是陷入這樣的境況:一部分“幸運兒”工作越來越努力,而幾億人卻在失業。來自新經濟基金會(New Economics Foundation)的安娜•庫特(Anna Coote) 提出的措施還要激進,她在2010年發布的報告《21小時》(21 Hours)中,建議削減每位工人的實際工作時間,以便讓大家能更公平地分享日趨有限的工作。今年元月份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舉行的一場討論會上,庫特建議把“工作過度、失業、過度消費、高碳排放、低福利、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缺乏維持一定生活水準的時間、相互關心以及純粹享受生活”等社會、經濟以及環境的“失衡問題”一同處理。接下來,我們聽到了《大蕭條下的生活經濟學》(Plentitude)一書的作者朱麗葉•肖爾(Juliet Schor)教授精彩解釋了為何即便從純經濟術語角度說,“超負荷、超時工作”(處理經濟衰退的常規做法)是得不償失。
還有一項無所包羅的失衡伊里奇從未公開提及,但在每處都隱含提及到了,那就是目的與手段(或者說形而下與形而上)之間的平衡問題。現代社會的成就(的確令人可疑)就是把目的變成了手段。所有一切都變成了技術性挑戰——如何永生、如何到火星上開疆拓土、如何最終造出智能手機——美其名曰是為了無可爭議的進步;而在探索的過程中,進步的所謂目的反而喪失掉了。伊里奇提醒我們:人類的本性要求我們自己要置疑目的——我們是誰?應該如何讓個體與集體都過上好日子——而不是僅僅去追求手段。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